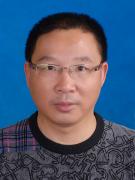火车上
一条草绿色的毛虫努力往前方爬着,众多微凸的纤足并不表示它的速度就有多快,相反,它的爬行愚笨而缓慢,仿佛一个垂暮的病人。它弯弯扭扭地爬着,背脊似一条微波起起伏伏,每爬一小段,它就要停下来歇歇,小小的口器却又贪婪地咀嚼吞咽面前的细草嫩叶,一边从微洞的肛口里排出几粒小小的粪便,再又做出努力的样
2015-03-15 18:5919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拂着湘南山区,也吹到了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其时我已是少年,故乡开始田土山包产到户,各家从此真正有了掌控自家生产生活的自主权,勤劳致富有了好盼头。似乎一夜之间,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为之一新,变得容光焕发起来,脸上多了几分兴奋与笑容,做事的劲头也更大了。
村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
2014-12-02 15:05广州的春天似乎多雨。1993年春节一过,我就跟随村里一班人来到广州郊区一个小镇,在一处农贸市场的建筑工地打工。虽然我在学校学的是建筑类专业,但干砌砖头的活还是外行,挂线行砖,抹浆勾缝,总是笨手笨脚。有一次,一个巡查的广东包工头来了,看到我砌的砖墙下掉落了不少砂浆,劈头盖脸就把我一顿大骂,好在我听不懂
2014-11-23 15:16在青山与青山之间,现在有时还能看到一座座高大的混凝土渡槽,有如多跨的拱形长桥,从这边的山头横跨到那边的山头。水从渡槽里临空流过,跨越底下的田野、沟谷或道路,流向前方曲折的水渠,流向沿途的村落,流向广阔的田野。清流甘冽,草木因之葱茏,禾苗因之欣欣而向荣。
这样巨大的渡槽,在我家乡村庄那方区域里并不
2014-11-23 07:44就如同村里那些古旧的老宅子,传到我们这一代时,几乎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建于何年何月。村北的油榨坊也是这样,从我小时候第一眼看见它,就是那副模样:黑墙黑瓦,古旧孤独,但不残破。能够知道它的年岁的,大约只有它身旁那几棵需一两个成人合抱才能围住的古枫古柏,只可惜古枫古柏并不像董永遇到的老槐荫树那样长个嘴巴能
2014-10-19 06:53按说,每天放眼所见,总离不开各种树木,池塘边的苦楝和垂柳,老井旁的苍柏,锦川两岸钻天入云的高杨和阔叶的梧桐,再远处,是山山岭岭的油茶树杉树松树和山苍子树,这种种树木,都已是司空见惯。可是,当看到村里有的人家空坪里长着一棵大桑树,有的屋旁长一棵大鸡爪树,或者棕叶树,或者香樟树,或者桂花树,而这些树却是
2014-10-02 10:24黄珠子花(栀子花)开的时候,周边的山山岭岭,整日都有村里的大人和孩子提着大篮筐和小篮筐,采摘这种喇叭状的洁白的花朵。
这是一种丛生的小灌木,我们那时叫做黄珠子树,大约是因为它那成熟的果实色泽金黄,且圆如指节之故吧。村后的后龙山和村北的枞山里,长着密密匝匝的高大乔木,那些散布在乔木周边,宛如抱着一
2014-09-28 12:38一年中,石板巷子里最热闹的日子,当属盛夏时节。
如果把老村的瓦房子比作是黄鳝藤上的叶子,那么黄鳝藤上每一根粗粗细细的枝枝丫丫,都是瓦房子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青石板巷子。在高而笔立的青砖墙下,石板巷显得十分逼仄,若是成人伸开双臂,两个手掌足以在两面墙上紧紧地撑住。而那时以我童稚的眼光看来,却是十分宽
2014-09-22 13:03晚稻收割之后,天气晴和,锦川两岸的田野顿时空旷起来。这个时候,一些放干了水,并经过多日晾晒后的稻田里,整日有人弓着背在用草刮子刨田埂上的杂草和田里枯黄的禾蔸,将一条条原本杂草丛生的田埂,一丘丘禾蔸密布的稻田,修整得干净而精神。傍晚时分,刨好的杂草与禾蔸连同粘连的泥土,已在稻田的中央堆成一个大而高尖的
2014-09-21 13:02母亲说,七蜂八蛇,七月的蜂八月的蛇是一年中最毒的,因此常警告我不要逗蜂惹蛇。这个时候正值盛夏酷暑,是放暑假的日子,而我每日的工作就是跟同伴们上山捡柴,与蜂与蛇相遇,那是稀松寻常的事情,尤其是黄黑花纹相间的吊脚蜂,几乎无处不在。
那些日子,嘴馋几乎是我们每个人的通病,上山捡柴的路上,到溪河里翻石头
2014-08-31 17:56- 上一页 1234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