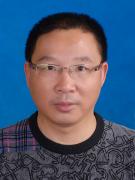有一天夜里,吃了夜饭后,荤黄的电灯下,父亲坐在墙角上,吸了几口短烟筒里一红一暗的土烟后,开腔了,又把准备批地建房的打算提上了议程。全家人顿时兴奋起来,我也刚好趴在长凳上写完作业。一番热烈讨论后,父亲做出决定,事不宜迟,赶紧向生产队写报告。这项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其时,大姐已出嫁多年了,二姐三姐都
2014-04-10 20:15厅屋里住着五户人家。
这幢马头墙高耸的百年老宅不知建于何时何人,青砖黑瓦,前临水圳,宅后和南侧是青石板巷子,北侧建了一厢巴壁屋,也是青砖黑瓦,因此,进出厅屋里只有两条门,正大门和南侧门。正大门耸抵檐口,两扇宽厚泛黑的原木门页当有一两丈高,仰头看时,檐口的粉墙上画着像鱼又像龙的怪兽,张牙舞爪,十分
2014-03-08 21:36原野上又在编织芳草的锦缎了,
桃枝子已披上了粉红色的淡装。
河岸的李树摆弄纤细的腰肢了,
偷偷地摘了几颗星撒在绿发上。
蛙儿在空旷里此起彼落地唱歌,
鹅群在桥下的沙滩上梳妆打扮。
柳丝轻抚河面,一片柔软的猗涟,
燕子衔来了朝阳,哦,好一派晴和。
肥圆的峰峦,一片鹅黄,
2014-02-23 14:53春天的歌(十四行)
挂在柳梢掠过的燕子嘴边;
藏在蜂蝶起落的花丛间;
飘逸在白鹭翱翔的山巅;
振动在田野蛙儿国的琴弦。
伴着山溪,伴着流泉;
渺渺地在梅雨蒙蒙的河面;
吻响了渔人的斗笠乌篷船;
跳跃在山道上行人的小花伞。
柔柔地在花木的芽尖;
细细地在土粒疏松
2014-02-23 14:39四季泉声,是森林的协奏曲,是山村的田园歌。
当山村上空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当漫天的春雨哗哗地浇灌大地,当深黛的山林微染了嫩黄的颜色,是谁打开了春天的大门?山林间,原野上,小河边,无数大大小小的泉眼顿时喷涌而出,汩汩流淌。
山溪活泼起来了,它汇聚了每一棵树下,每一条石缝,每一粒土壤的涓涓清流,千
2014-02-22 21:22(21岁时的习作)
山村朝暮
一
在鸡鸣和鸟啼声中醒来,习惯地走到屋旁的禾场上,踢踢腿,松松筋骨。深深地吸口气,啊,多么清新湿润,甜甜的,夹着野花的芳香,和着泥土的气息。四周一片空濛,万物都沐浴在淡淡的晨雾里,那么安详,静默。天愈见的高远了,那淡淡的白云像水彩大师在蓝色的天幕上信笔掠过,
2014-02-21 19:56“床上教妻,席上教子。”在我小时候,父母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尤其是我也能跟随父母上酒席场中可以落座时,这话似乎说得更勤了。我也慢慢懂得了其中许多规矩,比如说,“坐有坐像,洽(吃)有洽像”,尽管八仙桌十分高大,我坐在长条凳上时双腿还在半空晃荡,但也得端正坐着,不得乱动,不得多言,只能坐在边席的下角,
2014-02-14 19:35黄孝纪
鲁迅在赠给瞿秋白的一副对联中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古往今来,知己是每一个人心中至真至纯至切的期盼,然而知己却又是可遇不可求,千千万万的人甚至穷其一生都无法拥有。亦因此,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知音之情才能逾越万古,永为人心所推崇。
当许老柏舟先生把他精心整理好的书稿
2014-02-06 18:44村前的小河没有名字,它像一条游走在田野上的大蛇,从上游的羊乌嘴村游来,然后又钻进了下游朽木下村,我的童年大致没有走出过这段游蛇的范围。事实上,村里人至今仍然都是泛泛地称之为“江”。我想,假如我能有资格给我记忆中已经远去的那段游蛇取一个名字的话,我愿意把“锦川”二字送给它。
那时我的锦川有着清秀而
2014-01-14 13:30结冰盖啷的日子,说话都能看见从嘴巴里冒出来白花花的热气,鼻孔里挂着的两条清鼻涕才刚用力吸了进去,立马又滑到了嘴唇边边,舌头一舔,抬手擦在了油光发硬的衣袖上。
母亲从园子里摘了一菜篮子大青叶菜来,进屋时声音有些发颤:“好厚的冰盖啷,手指骨都要断了。”我瞧大青叶子上的冰盖啷还在,从叶上剥下一大片拿在
2014-01-07 19:12- 上一页 1234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