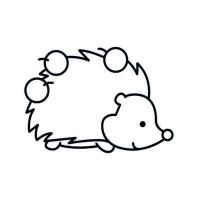没写过什么宏伟巨制,甚至连一篇像样点的文章都没有拿出手过,就那么几篇散文,发点小感慨,写点小回忆,那点东西不过是时光隧道里一丁点小到显微镜下才能显示的小虫。可气的是居然自己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一副文人胚子,原本就是为文字而生,骨子里就该跟文字打交道,这种心态持续过一段时间。
就像自己喜欢唱歌,有几
2016-12-16 10:07(一)
母亲过生日,亲戚朋友来了一大堆,大家有说有笑围坐在茶几旁。一群孩子来回跑,儿子跑累了停在封好的生日大蛋糕旁边,想起了今天是外婆的生日。停了一会儿,只见儿子把外婆从卧室里拉了出来,扶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然后两个小手抱着小拳头,一条腿跪在地上,有模有样地作着揖,“老奴给娘娘请安,肥妃娘娘万福金
2016-12-16 10:07儿子发烧了。当他姑姑打电话的时候,正坐着公交车、徜徉在林间小道、享受惬意春风的我们,再也无暇顾及眼前的美景了。
挂了电话,轻叹了一口气。丈夫问我孩子现在在哪里。我说离我们下公交车不远。他只说了一句,快到的时候提前打电话给他姑姑。我说好。
虽然嘴里不说,也没有埋怨,但能明显感觉到,彼此心里的慌
2016-12-16 10:05第一次见她不带口罩的样子,很美,猜不出年纪。
我送给她一个名字,叫“炸串西施”,问她喜欢吗?
她笑着说,人家西施是何等的美人儿,就我这模样儿可不行。
我说其实你真的很美。“西施”咱没见过本人,连照片都没有,单凭后人的想象,那多虚啊!你可是实打实的大美人儿,就在我眼前。
她开心地笑了,
2016-12-15 14:27一般人很难把“吃面”和“回家”联系起来。吃面在哪里都可以,回家后也不仅仅只有吃面啊!是的。可是对我来说,回家吃一碗母亲做的炝锅面是一件让我幸福百倍的事情。
记得在外读书那几年,坐火车回家很少能正好赶上饭点,要么是母亲刚刷了碗筷,要么是距离开饭还很早。可是每次到家都饿得要命,因为火车上人太多实在难
2016-12-15 14:26萧山来天津了。杜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参加学校合唱团的彩排,下周就要去上海参加比赛了。我问他萧山为何而来,他说他得了白血病,在天津血液病医院住着。
电话是怎么挂的,我都忘了。只记得当时眼睛里一直有泪涌出,涌出,再涌出。混混沌沌回到宿舍的时候,敏告诉我,下午有个姓杜的同学打来好几次电话,问
2016-12-15 14:26某晨,阳光洒满不大的屋子。窗边,摆满了各种绿色的盆栽植物。细细的叶子在温暖的阳光里自在地伸展着,自由地呼吸着。偶尔有一丝儿小风从窗外吹入,晃动的叶尖将刚被主人喷洒的水珠抖落下来。
靠窗的一张大大的桌子,几张纸被钉在一起,一支笔摆在纸张的右边。桌的两边各有一把椅子,东面是来拿文书的人短暂停留的,主
2016-12-13 16:04经历了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灾病,整个人突然幡然醒悟了很多,平静了很多,奢望和顾念也放下不少。外婆生前总爱念叨:“健康是福”,以前听多了也不觉如何,现如今想来,九十多岁的老人经历了多少事,该放的都放下了,该忘的都忘记了,能寿终正寝即是大福了。
躺在病床上的很多个小时里,枕着病痛,连呼吸都一股子苏
2016-12-13 16:04古城兖州的日新月异,让这个三线城市都不算的小城也热闹起来了,早点铺子多了很多洋式快餐、粥铺,种类和花样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吃过几家以后,反倒觉得儿时一直吃着长大的老街巷子里的“辣汤油条”依然是我所钟爱的早点。
我是地地道道的老兖州人,城乡结合部地带出生长大,所谓“进城”也就是十分钟左右的自行车路程
2016-12-13 14:18大年初九,裹着凛冽的寒风,我来到火车站,准备去淄博参加大学舍友阿吉的婚礼。她在我们宿舍排行老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小妹。八年前她给自己设定了三十岁结婚的目标,如今顺利完成了。
高高的站台上,一群拎着背着各种行囊的人们你推我搡地排着不算整齐的队伍等待着火车的到来。一群到全国各地奔波游走的艺考生,穿着
2016-12-13 14:17- 上一页 1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