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有名的经典散文
丰子恺原名丰润,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1] 和翻译家。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丰子恺有名的经典散文,供大家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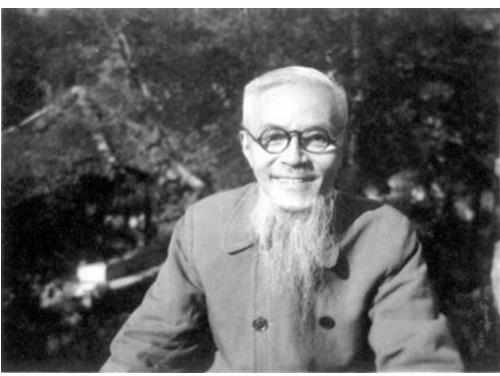
丰子恺有名的经典散文:梧桐树
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它们的主人,对于它们的局部状态也许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全体容貌,恐怕始终没看清楚呢。因为这必须隔着相当的距离方才看见。唐人诗云:“山远始为容。”我以为树亦如此。自初夏至今,这几株梧桐树在我面前浓妆淡抹,显出了种种的容貌。
当春尽夏初,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好像一堂树灯,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巧: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其渐,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它们的枝头疏而粗,它们的叶子平而大。叶子一生,全树显然变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见绿叶成阴的光景。那些团扇大的叶片,长得密密层层,望去不留一线空隙,好像一个大绿障;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叶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无过于梧桐了。芭蕉叶形状虽大,数目不多,那丁香结要过好几天才展开一张叶子来,全树的叶子寥寥可数。梧桐叶虽不及它大,可是数目繁多。那猪耳朵一般的东西,重董叠叠地挂着,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窗前摆了几枝梧桐,我觉得绿意实在太多了。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
一个月以来,我又眼看见梧桐叶落的光景。样子真凄惨呢!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吹,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搿几根枝条,回复了春初的面目。这几天它们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经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了的光棍,样子怪可怜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诗:“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现在倘要搜集它们的一切落叶来,使它们一齐变绿,重还故枝,回复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间一切支配者的势力,尽了世间一切机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黄转绿世间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叶,尤其是梧桐的落叶。
但它们的主人,恐怕没有感到这种悲哀。因为他们虽然种植了它们,所有了它们,但都没有看见上述的种种光景。他们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们的根干,站在阶前仰望它们的枝叶,为它们扫扫落叶而已,何从看见它们的容貌呢?何从感到它们的象征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可知艺术也是不能被占有的。
丰子恺有名的经典散文:春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长在人间。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春!”你听,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惺忪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我积三十六年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
梅花带雪开了,说道是漏泄春的消息。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栊内,战栗地站在屋檐下,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
再迟个把月罢,就像现在:惊蛰已过,所谓春将半了。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像因为我偎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寒暑表激烈地升降于三十六度至六十二度之间。一日之内,乍暖乍寒。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淇淋,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料峭”的滋味。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干燥的鞋子往屯拖泥带水归来。“一春能有几番晴”是真的:“小楼一夜听春雨”其实没有什么好听,单调得很,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春将半了,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点舒服,只教我们天天愁寒,愁暖,愁风,愁雨。正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罢?有的说“春在卖花声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确。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么?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呢。
可知春徒美其名,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寒暑表上的水银爬到temperate上,正是气候最temperate的时节。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须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慰人心目。古人词云:“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出。”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我觉得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造物者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蘸些胭脂、硃磦,轻描淡写。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蘸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地涂抹,使屋屋皆白,山山皆青。
这仿佛是米派山水的点染法,又好像是Cezanne风景画的“色的块”,何等泼辣的画风!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园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工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
讲求实利的西洋人,向来重视这季节,称之为May(五月)。May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人间有种种的娱乐,即所谓May-queen(五月美人)、May-pole(五月彩柱)、May-games(五月游艺)等。May这一个字,原是“青春”、“盛年”的意思。可知西洋人视一年中的五月,犹如人生中的青年,为最快乐、最幸福、最精彩的时期。这确是名符其实的。但东洋人的看法就与他们不同:东洋人称这时期为暮春,正是留春、送春、惜春、伤春,而感慨、悲叹、流泪的时候,全然说不到乐。
东洋人之乐,乃在“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新春,便是那忽晴、忽雨、乍暖、乍寒、最难将息的时候。这时候实际生活上虽然并不舒服,但默察花柳的萌动,静观天地的回春,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故西洋的“May”相当于东洋的“春”。这两个字读起来声音都很好听,看起来样子都很美丽。不过May是物质的、实利的,而春是精神的、艺术的。东西洋文化的判别,在这里也可窥见。
丰子恺有名的经典散文:湖畔夜饮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 CT,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一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倾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 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的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饮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剪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也不想去剪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有些“专家” 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做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她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
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 “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姐姐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上揭去,制了锌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
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前,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帐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帐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帐,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帐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丐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丰子恺相关散文文章:
1.丰子恺经典散文推荐三篇
2.丰子恺经典语录
3.丰子恺的散文名篇
4.丰子恺散文名句
5.丰子恺散文感悟

丰子恺有名的经典散文的评论条评论